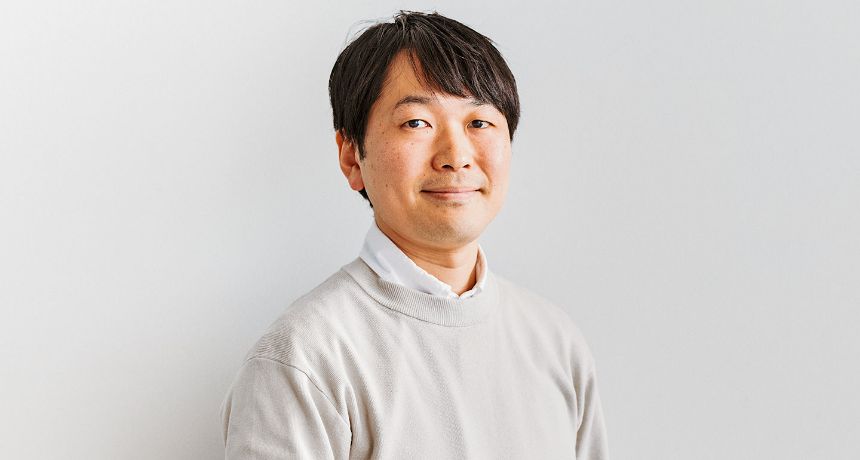為了實現正義。跨越分歧、朝向努力就有回報的世界
如何才能改善社會?如何才能解決社會的結構性問題?帶著這些問題,船山靜夏在商社、大使館及NGO等領域,甚至在成為自由工作者的那段時期也參與社創,在國際合作的各個領域,累積了超過十年以上經驗的她,於2023年4月加入了TYPICA,並在同年的11月晉升為執行董事。
目前,身為社長辦公室的一員,她致力於打造讓每一個工作同仁生活感到充實,並能發揮自身潛力的“超級企業”環境。同時,她也負責推動永續發展及政府資金專案的營運工作。對船山而言,TYPICA 是「目前我所知,最接近理想的地方」。

TYPICA 可以超越分歧
船山在大學時代有段難以忘懷的回憶。在一堂特別講座中,她聽到了一段關於東南亞某國船民(乘坐漁船和遊艇等小船逃離故鄉的人們)的故事。
《當我逃離祖國,與其他難民一同搭乘小船漂流在海上時,一艘日本船正向我們駛來。我心中滿懷期待,想說他們肯定會救我們到日本吧。然而,那艘船卻不知何故突然掉頭離開了……》
雖然當時的記憶已經有些模糊,也許早已在我腦海中重新拼湊過,但從那個人口中說出的“But the ship turned around.”(船卻掉頭了。)這句話始終深深烙印在船山的腦海裡,揮之不去。
「想像當時的情景,我想,船上的船員或許真心希望能幫助這些難民,卻因法律或制度的限制而無能為力。僅僅想到他們在不得不放棄眼前這些人的那一刻,內心所經歷的掙扎,就讓人心痛不已。這也不禁讓我思索:究竟該如何來解決導致這種情況的結構性問題?」
為了尋找這個問題的答案,船山在大學畢業後,進入了一家專門協助ODA(政府開發援助)的商社工作。隨後,她加入駐奈及利亞的日本大使館,參與救援事業的策劃與管理。在那段工作期間,她深刻體會到自身缺乏系統性的知識,於是決定進入研究所,研究了非洲的社會創業。之後,她加入了專門援助國內外因自然災害或紛爭而陷入人道危機的人們的NGO「和平之風日本」(Peace Winds Japan),在那工作三年半。負責運營由日本外務省及聯合國資助的救援項目。
然而,由於規則與資金的種種限制,有許多領域無法深入探索,所能產生的影響也十分有限。當今世界以主權國家為基礎運作,許多問題往往會牽涉到內政,而一旦無法介入,即使是聯合國也難以徹底解決根本問題。看來唯有擁有穩定且獨立財源的企業才有辦法了吧,船山出現了這樣的想法,選擇了成為自由工作者,並積極投身於服務發展中國家BOP(金字塔底層)人群的社會企業。然而,即便如此,她仍難以想像,這樣的事業能夠突破區域限制,實現跨洲際、全球化的規模。
「在發展中國家,我們確實取得了一些成果,如今也已成為一家持續成長的企業。然而,一旦被歸類為“社會企業”,似乎就能感受到其侷限性。讓世界變得更美好,似乎與一般民間企業的經濟活動存在著某種矛盾。我感覺到,關心社會問題與國際合作的人,與對此漠不關心的人之間,似乎存在著一道難以跨越的鴻溝。」
關於這一點,TYPICA 是一家將生豆直接流通到烘豆師與咖啡愛好者手中的「一般企業」,但同時也藉由這項事業,致力於解決生產者的貧困與人權問題。換言之,TYPICA 自然而然地將社會責任融入其商業模式之中,這正是讓她感到特別之處。
「目前,我們正在社長室推動這項工作。但未來,我期待能突破政府或國家的框架,讓像 TYPICA 這樣的企業聚集成一個聯盟,擁有強大的發言權,就能超越分歧,跨越彼此之間的鴻溝,著手解決社會的結構性問題。」

創造一個努力就有回報的世界
在國際合作領域,有一句廣為人知的箴言:「授人以魚,不如授人以漁。」的確,提供金錢或物資能在短期內拯救陷入困境的人們,但從永續發展的角度來看,這種方式卻要打上一個問號,值得深思。因為當人們習慣依賴他人的援助,或是不需付出努力就能輕易獲得資源時,往往就會變得越來越怠惰。
「我個人並不認為每個人都應該以相同的方式獲得救助。例如,在難民救援的現場,我曾聽聞過少數人利用不正當手段,領取生活補助的情況。實際上,有些人明明住在家中,卻在難民營登記為難民,然後領取救援物資,將省下來的生活費存起來。」
「在日本,由於政策的不完善,一些弱勢群體往往會拿著標語參加示威遊行,要求改變。制度上確實存在問題,這樣的行動或許是一種解決途徑,但對我而言,我認為重要的不是單純期待制度的改變,而是應該先具備依靠自己力量,開創未來的態度。」
即使要改變社會,歸根結底是取決於個人如何生活。一個人的努力與否,雖然會受到出生環境的影響,但我覺得要幫助人們超越這些限制、推動人們向前,靠得不是制度的救濟,而是情感。」
船山從大學時代便懷抱著「我想看到正義的實現」的願景,這個理想始終未曾改變。雖然她所加入的組織和解決問題的方法各有不同,但每一次的選擇,都是為了實現自己的願景,並在當時做出最合適的決定。而現階段,TYPICA 是船山認為最適合的方式。
「透過這個平台,小規模生產者辛勤栽培的咖啡能夠獲得公正的評價,並以合理的價格銷售,從而改善他們的生活水準。家庭經濟變得更加寬裕,孩子們得以上學,未來也能擁有更多夢想。我感到TYPICA 有能力創造出一種讓「努力得到回報」的正義模式,並將這樣的模式傳遞到世界各地。」
孩子無法選擇自己出生在哪個國家、社會或家庭。現實是,孩子的一生往往會因為國家的局勢、家庭的經濟狀況、文化資本以及父母的社交圈等因素,形成難以彌補的差異。
「有時我會想,如果我是在不同的環境中出生和成長,或許會過著截然不同的生活。例如,我從未想過自己能成為醫生或學者,但如果身邊有這樣的榜樣,我可能會自然而然地走上這條路。我認為,人生的變化取決於那些無限的可能性裡,有多少能夠近在眼前,成為你現實生活中的選擇。我想這也是為什麼,當年在大學時,親耳聽到那些被剝奪了可能性的難民講述他們的經歷,深深觸動了我的心。」

在「自我」與「世界」的夾縫中搖擺搖擺
賦予船山強烈正義感的,正是來自於她那不尋常的家庭環境。她父親是一個不在意他人眼光,幾乎不工作,酗酒後對家中的貓施暴的人,一個「對有常識的大人來說無法想像的行為古怪者」。每當家電量販店等商店有限量特賣品時,他總是從清晨就開始排隊,如果商品售罄,他會不停抱怨,直到爭取到自己想要的東西,讓人覺得非常麻煩。
這樣的父親,怎麼可能讓她產生敬意呢?儘管在生理上他是她的父親,但她無法認同他是家庭的一部分。小學時,她常對父母說:「趕快離婚吧。」最終,父母離婚了,她、母親和姐姐,在進入國中那個春天,一起搬進了新家。
「我想,在我們搬走之後,我對父親的感覺逐漸發生了變化。對我而言,父親曾經就像是那種想擁有卻無法得到的奢侈品。曾經有一段時間,我一直在追逐他那不真實的影像,但自從十多年前見到年邁的父親後,我開始淡然地覺得,他變成了一個未來需要默默守護的人。
或許正因為在這樣的家庭環境中成長,我從未想過選擇依賴男性的生活方式。甚至在我20歲時,我曾公開宣佈過:『我不婚。』然而,最終我還是在二十多歲時決定結婚,我認為這是成為一個負責成年人的一部分,但或許也受到了根深蒂固的社會觀念的影響吧。」
儘管船山強烈渴望過獨立的個人生活,然而另一方面,她也難以擺脫社會習俗和刻板印象的困擾。在90年代中期,「也有單親家庭」的概念尚未像今天這樣普及。例如,在小學的課堂上,老師常會問:「大家家裡有幾個人?」並讓學生舉手回答。而以「家裡有爸爸是理所當然」為前提,讓她難免感到一股強烈的違和感。
人們心中根深蒂固的觀念和社會常識,往往在日常生活中的細微之處悄然顯現。當時,船山利用學貸進入早稻田大學的政治經濟學院,曾在打工面試中被問過:「妳爸爸是銀行員工還是商社人員?」對方或許並無惡意,但每當船山面對這樣無心的偏見問題時,她內心便難以平靜。
「這些問題背後隱藏的含意,似乎是在暗示他們認為我來自富裕家庭,肯定是在無需為生活奔波的環境中長大的。然而,這些問題忽視了我自己努力的成果,更忽略了我母親日以繼夜辛勤工作的付出,這讓我感到非常不舒服。更何況,每當我談起自己的家庭情況時,他們總會尷尬地看著我,彷彿我說了什麼不得體的話。我覺得不公平的是,父母的離婚只是事實而已,為什麼無法不帶評價地接受我的家庭情況呢?這讓我感到十分不公平。」

成為他人的榜樣
經歷過這樣的時代,船山如今希望能成為他人的榜樣。她希望大家能看到自己的經歷,激勵那些和她一樣來自單親家庭、經濟困難,或是在社會潛規則中掙扎的女性與年輕人,為他們帶來力量與鼓勵。
「我的成長之路並非傳統的平步青雲,職涯也經歷了不少波折。然而如今,我能夠在一家深受社會高度評價的成長型企業中,成為完全遠距工作的管理層人員,實現這樣理想的工作方式,這讓我感到非常踏實。
我不再擔心這是否與社會期待的生活方式不同,因為自己的幸福是由自己決定,是靠自己的努力爭取而來— —雖然我想毫不猶豫地說出這些話,不過有時我還是覺得,自己似乎無法完全擺脫那種“應該這樣”的社會標準。」
船山強烈感受到反抗社會常規的代價,是在結婚時選擇保留自己姓氏的時候。只有約 5% 的夫婦是由丈夫選擇改姓(截至2022年),排除入贅的話,這種情況更是罕見。
「我曾經在對表達『我希望保留自己的姓氏』這件事上,煩惱了很久。除了傳統觀念外,選擇丈夫的姓氏並沒有其他合理的理由。當時我認為,在這樣的情況下,如果我不堅持自己的選擇,那麼一輩子都沒有資格對賦予女性權力的問題發表意見。所以,我決定鼓起勇氣,坦誠地表達我的想法。」
「雖然丈夫欣然同意,但他的父母始終無法理解,這讓我們的關係變得有點緊張。當我與同齡的男性友人談起這件事時,他們也會感到驚訝,說『怎麼會這樣?』然而,從本質上來看,如果男女平等,這樣的選擇本不應該成為困擾,也不應該引發人際關係的衝突。」

母親的作品──我
船山自己希望成為他人的榜樣,但她從來沒有遇過身邊可以作為榜樣的人。儘管在大學之前,她從未對將來有過任何夢想或目標。不過,她擁有“輝煌”的履歷:早稻田大學政治經濟學部畢業,並在牛津大學研究所獲得碩士學位。
「如果只看這些履歷,可能會覺得我是個“努力的人”,不過我完全不這麼認為。也許是因為我的記憶力比別人好,在小學的測驗中,我基本上不用特別努力就能拿到接近滿分的成績。至於大學,感覺只是按部就班地學習,就順利考上。老實說,我想自己或許只是比較有天賦。
如果說我能在不知不覺中努力工作,那麼這種態度的養成應該歸功於母親所創造的環境。我在那個不抱怨、勤奮工作母親的身邊長大,或許也因此自然而然地學會了努力。總而言之,今天的我能成為這樣,完全是母親的培養與影響,真正努力的人是她。可以說,我是母親的作品與成果。」
對船山來說,推動她前進的動力,源自於希望有一天能讓母親過上輕鬆的生活,並實現她的願望。母親只有短大的學歷,且沒有任何專業資格或執照,這使得她在轉職時處於劣勢,能找到的工作選擇非常有限。在這樣的情況下,母親一方面要靠自己的雙手撫養兩個女兒,一方面又為了找到條件更好的工作而四處奔波。至今,母親僅憑一雙手獨立撫養兩個女兒的情景,仍然深深烙印在她的記憶中。
「我從來沒見過像母親那樣拼命工作的人。早上,她總是先做好我們的便當,然後比我們早出門;而晚上,我幾乎不記得曾一起吃過晚餐。印象中,即使是週末,母親也很少完全休息一整天。
母親不僅辛勤地將我們養大,還讓我和姊姊擁有了一個正常的童年。她一手包辦所有家務,從不對女兒有任何要求。當我在考試中取得好成績時,她會表揚我,讓我相信努力就會有回報。 在我的職業生涯中,她也一直支持我的每一項選擇與決定……為了報答母親那無私奉獻的付出,我希望自己可以成為一個能為下一代留下些什麼的人,而我認為TYPICA正是實現這一目標的理想場所。
「與其擁有自己的孩子,我更希望以身作則,為下一代做出更廣泛的貢獻。身為“母親作品”的我,深感既然還有一生想要追求的夢想與目標,就不希望將人生的重心完全放在孩子身上。在這個多元發展仍停留於口號層面多於實際行動的時代,尤其是身為女性的我們,我們該如何為社會貢獻力量,又能留下什麼樣的價值?透過我的生活方式,我希望能展現另一種可能,並讓母親為我所做的事感到驕傲。或許,這正是我能給母親最好的回報。」